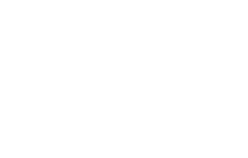【戏说英国】在英国坐船去小岛跑通勤那些日子
文/纪 杨
谁能想到若干年后,我会来到英国生活呢?谁又能想到对英国的最初印象,是从一个小岛的样貌构建起来的呢?并且,更令人意外的是,我过了一段坐船去小岛跑通勤的日子。就在一年以前,我的工作地还是在北京和迪拜这样的地方。但这也注定我平白多了一个视角——小岛人的思维,从一个边缘的、甚至有些隔绝的岛屿的立场,去考虑外面的世界。而不仅仅从傲慢的大城市人的立场看待世界。
六年前的六月,我从北京飞到伦敦。那是我第一次来英国。当飞机盘旋飞行等待降落指令时,我极力望向窗外,寻找那些耳熟能详的伦敦地标,诸如伦敦眼、大本钟什么的,事实上我什么也没看清楚,然而我还是看到一条蜿蜒的河流——泰晤士河,从东到西,曲曲折折,把城市分成两半。那时候对一个首次到访这座城市的人来说,任何一点微弱的提示,都能让我感觉到一丝熟悉的气息,让这座完全的陌生的城市不那么陌生。第一次来伦敦,我在一个邮编为SW5的酒店住了一晚,因为地段的原因房价不菲,也因为价格“不菲”(120英镑,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伦敦的便宜住宿),房间小到打开行李箱便打不开房间门。
次日一早,我搭上从滑铁卢站开往南安普顿的火车,因为我此行的目的地是英国南部的一个小岛——怀特岛。若干年后,当我回想起来,去一个小岛上工作,再多的心理建设也不足够。
然而,我在伦敦住的那晚,并不是普通的一晚。那天正好是2017年6月3日,伦敦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驾车冲进桥上正在行走的人群中,造成数人伤亡。对于伦敦这座闻名遐迩的大都市,我还没来得及品味传说中的美妙和历史感,便带着惊恐和疑惑离开。
说起坐船跑通勤的经历,要从南安普顿说起。南安普顿是汉普郡的首府,位于英国南部,那里有渡轮通往怀特岛。放下行李后,我溜达到市中心,想顺便问一下明天在哪儿乘船。我选择了一位年纪约70岁上下的老者,他看起来神清气爽且乐于助人,更重要的是,我凭直觉判断他是本地人。那时我们站在南安普顿高街西港(West Quay)和老城门之间一处下沉广场中央。他指着城门外方向,告诉我去TOWN QUAY坐RED FUNNEL的船。以我的英语词汇量,理工科6级,雅思5.5水平,完全没能理解town quay这个词的含义。我期望听到类似港口,像dock, pier, jetty, harbour, port, marina之类的单词,总之能上船的地方。然而,我会的那几个词儿一个也没听到。可能首先我没能想象出像南安普顿这样一座首府城市,在英文中居然只配一个town,当然我后来才知道一个地方被称为镇(town)还是城市(city),在于那个地方是否有一个大教堂(Cathedral)。像温彻斯特,城市虽然小但有一个温彻斯特大教堂。而town一词在我的理解中相当于中国农村某乡的一个小镇,比如乌镇是一个water town 。再则,我也无法理解quay一词意思就是游客码头。另外,RED FUNNEL是红烟囱,还是红漏斗?那又是什么鬼?
当然,次日一早,我顺利地找到码头,以及船运公司红烟囱(RED FUNNEL)售票处,买了一张往返船票,及时登上了开往怀特岛的快艇。因地方不大,我预留了足够多的时间以防找不到,但事实证明,一切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得多,也方便得多。
想了解怀特岛,最好打开一张可以一再放大的网络英国地图,或者一张怀特岛地图,因为很难从一张纸制的英国地图上看清怀特岛的面貌。怀特岛,英文Isle of Wight,下面还有一行字: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意思是“杰出的自然风景区”,坐落在英国最南端,岛的北部与英格兰主岛中间隔着索伦特海峡,南部隔着英吉利海峡与法国隔海相望。岛在伦敦的正南方向,地图的最下方。有两种方式去怀特岛,一种是从南安普顿始发的快艇和一层装货/车辆,两层坐人的大渡轮,到达岛上的考斯(Cowes), 两者的区别在于快艇red jet 停靠Cowes Harbour,而大渡轮停靠在东考斯码头East Cowes, 考斯与东考斯之间一河之隔,河的名字是River Medina。这条河从海峡进入岛屿,径直向岛的心脏地区绵延十几公里,直插入岛屿中心新港New Port。另一种到达怀特岛的方法是从朴茨茅斯出发,这一处码头应该应该使用Port,因为朴茨茅斯被称为Port City,一座地道的港口城市,航线众多可达法国、西班牙和其它岛屿,也是英国海军军事基地所在地,从此处出发到达怀特岛的菲什本(Fishbourne)那里有一个Fishbourne pier。而考斯是我将要工作的地方。所以,未来我将不断地从南安普顿的镇码头出发,乘快艇或渡轮去小岛,开始我的通勤日常。
对于从小生活在内陆的人来说,对海和岛常常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在想象中把海洋和岛屿无限神化、美化、浪漫化。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有一天,我将在真正的小岛上工作。而那段经历始于我在英国生活最初的那段时间,什么都新鲜。
第一次坐船,同行人是一位威尔士小伙子,他从曼城飞到南安普顿,在火车站换乘到码头的接驳车,有船票的话免费,然后和我一样赶到镇码头登上同一班快船。在二十分钟的航程中,我们谈论着英国的天气、海岛,以及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像海上的雾一样尚且无法看清的未来。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大部分工作日,我重复着这样的路线:南安普顿Southampton =>镇码头Town Quay => 渡轮Ferry =>东考斯East Cowes =>锁链摆渡船Chain Ferry => 考斯Cowes =>办公室。一天之中穿过两次索伦特海峡,两次麦地那河。这听起来挺别致的,跑起来非常花时间。
一开始我坐快船,赶时间。船上大多是来来往往通勤的人。如果坐快艇,从码头出来便是考斯的高街,步行街,我琢磨着脚下的铺路石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一片沧桑的历史感,在雨天里格外滑溜。从码头出来,在这样黑漆漆的石头路上走不了一会儿,路过COSTA咖啡馆和一家二手商店,看到玛莎食品超市便要向右转,然后向上顺着Seaview Road, Moorgreen Road蜿蜒而行,然后在54号房子处左转。在起初看起来没啥区别的街道和矮房子之间穿行,让我不迷路的唯一办法就是死硬背那些马路名称和门牌号。
这与我以往的工作经历都不同,来到发达国家,却不再是高楼大厦。在英国小公司或工厂都在很小的工业园区里,园区的隔壁是仓储区,对面是棒球厂,四周一望无际。
之所以改坐慢船,周转折腾有两个原因,一则时间虽然从20分钟增加到一个小时,但好处是平稳、安全。快艇遇到风浪颠簸厉害,并且经常停运。二是买年票的话,坐慢船交通成本低得多,单程票价也不到10英镑。船上有WiFi可以工作,还有一个酒吧和观景台,必要的话在上班途中还可以感受度假的感觉。坐慢船是受到跑通勤的同事马修的启发。除了时间长了个把小时,唯一不便之处就是我得再坐船过麦地那河。因为轮渡停东考斯,要去考斯镇必须过河。
这就不得不搭乘连接麦地那河两岸考斯和东考斯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索链船chain boat。在英国,chain boat 也叫 floating bridge。这对我来说是新鲜玩意儿,河虽不宽,不到50米,但没有桥。一条长约15米左右的汽船,可以把车开上去,能装十辆八辆车,人车分流,船靠底部的铁锁链传动,慢吞吞轰隆隆地从此岸蹭到彼岸。票价50便士每人每次,车要1英镑50便士。每次从大船下来,走几分钟再接着等船从对岸挪腾过来时,我都忍不住想,为什么就不能修座桥呢?这里来座石拱桥不方便吗?后来发现不仅我这么想,印度同事阿时力也是这么想的。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来英国以前认为英国是发达国家,没想到还在使用这么落后的破东西。他因为老婆学医入职岛上全科医生,所以不得不在岛上找份设计师工作。享受度假工作不分家之余,抱怨一下英国的守旧和执拗,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吧。毕竟下班时带上同事散养的鸡下的土鸡蛋回家也很快乐!
自从在岛上工作以来,我慢慢开始适应坐船上班的通勤生活。带了一个宜家的大杯子用来喝茶。但不到两天我发现,行政部的黎明大姐捧着我的杯子在喝茶。她叫Dawn,名字特别好听,人也热情,她已经把我的杯子混入厨房茶杯大家庭里了。可这不符合我的卫生习惯。那天后,我喝完茶,没有把茶杯随意放进洗碗机,而是洗了放回我的桌子上,以免混用。后来,黎明大姐便不再收我的杯子。但有时她泡茶的时候仍然问我:Would you like a cup of tea(要不要来杯茶?)? 我看了看手边的杯子,说:谢谢!不用了。
在小快艇和大渡轮之间还有一个区别,乘快艇的大多是商旅人士,西装革履,气度不凡;而乘大船的人偏休闲出行,车子停在下面甲板上,一家人背着抱着上楼坐定,有猫有狗,大人喝酒,孩子吵吵嚷嚷。特别是在暑假期间,更是热闹极了。即使工作,我也不讨厌坐在他们中间,感受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这在英国可谓是不可多得的烟火气息。
不过,想起以前去鼓浪屿和普陀山两座岛时,也是排队坐船,岛与陆地间也没有修桥。据说是为了保护岛上的自然生态,不过度开放自有缘由。然而,这个运营了几十年的索链船却另有原因。
一天下班后,我和同住在南安普顿的同事一起等船,正赶上帆船经过,高达十几米的桅杆上挂着涨满风的风帆,沿河滑过,帆船上的水手一边向开锁链船船长致意,一边向瞭望塔楼上的人致意挥手。等待上船的车和人越积越多,大家都耐心等待,行注目礼。怪不得,不修桥。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原因。同事说:桥两边的建筑由来已久,如果修桥需要高度足够,那么引桥会很长,那样就会影响那些建筑。原来造桥事小,但要像伦敦塔桥那样适时开合,允许高桅杆帆船经过才行。而怀特岛上最大的盛事便是每年夏季的帆船赛事了。
在方便通行与让帆船经过这件事上,英国人的选择显而易见,没有人想放弃任何带来快乐和有价值的东西。慢慢地,我发现在英国人的价值排序上,发展和效益,远不如娱乐重要。
在英国,似乎没有人想改变什么。一切从旧如简。慢慢地我也适应了慢节奏,工程进度不再十万火急,产品交付期无论是90天,还是180天,也不再令我抓狂。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不再坚持使用自己的杯子喝茶。在通勤这件事上,我也变得更有耐心,在那些等待的时间里,悠然地看渡轮和锁链船缓慢地靠近,再载着人们向着生活的下一个目的地,缓缓驶去。
作者介绍:纪杨,浙大理学院硕士毕业,在能源行业任高级工程师数年。六年前开始在英国工作生活。喜好艺术与文学表达,业余热衷画画、自由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