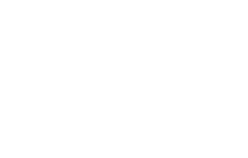【戏说英国】英国琴房奇遇记
作者:肖淳端
题记:所谓奇遇,是指某段经历前后悬殊奇大,主要表现在技能的迅速提高等。希冀奇遇,一般而言,源自弱者心理,反映了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小时候看皮皮鲁与鲁西西,就十分希望也能拥有小人博士,不用担心平时不用心学习而名落孙山,只要到考试那一天,把无所不晓的小人博士放在耳朵里,各种刁难的试题自然难不倒他,而我便轻而易举地一鸣惊人,从此备受老师校长的青睐,嘿嘿!于是,到处寻找过期的罐头,也一直舍不得开没过期的罐头。这样美好的愿望一直伴着我走过无数寒暑,此间也经历了无数次的考试。中学时迷上金庸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喜欢其笔下人物的种种奇遇。段誉偶然学会凌波微步,张无忌无意习得九阳真经……如此种种总让我羡慕不已,心驰神往。几经没有下文的守株待兔,我渐渐对此不再寄予殷切的希冀,偶尔回想起来,倒也为童年的天真稚气颇感自豪。再往后,幻想少了,生活趋于平淡。留英的日子也在这份平淡中一点点地流逝。学业上没有什么长进,人生阅历、文化感受上倒是烙下些许痕印,其中略具戏剧性的当属在琴房的经历,趁现在梦还没醒,给它画上翅膀,便也算得上是一段奇遇了。
学校校内座落有一个闻名遐迩的艺术中心,据说是伦敦以外全英最大的艺术中心,包括两家大型音乐厅、两所剧院、一家电影院和一个音乐中心,每年约有25万人到此参观。欧洲古典乐一直被认为是古典音乐的主流,从以C.W.格鲁克、G.F.亨德尔和J.S.巴赫为代表的前古典乐派,到德奥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20年代以J.海顿、W.A.莫扎特和L.van贝多芬为代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无不给古典乐史留下协调高雅、持久典范的辉煌乐章。英国有不少正统的音乐学校,比如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一般都是小班授课,音乐专攻,再加上与别国音乐交流频繁,本土乐团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民众所受的音乐熏陶也甚是浓烈。就学校的艺术中心而言,经常会有世界顶尖乐团和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前来演出。在艺术中心进进出出,和你擦肩而过的,很有可能就是某位名家“巨”人。比起国内同类演出,音乐会的票价并不昂贵。为了显示严肃音乐的非盈利性,也为了让高雅艺术更深入民心,音乐中心还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音乐会,大多是在中午举行,故俗称“音乐午餐”。由于囊中羞涩,我便成了“音乐午餐”的常客。
经常往音乐中心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儿的钢琴。音乐中心有9个琴房、1个演奏厅,其中有7间琴房免费向校内师生开放。以前在国内,大学最最吸引我的地方是琴房,虽然收费不菲,兼又简陋不堪,我还是心甘情愿解囊加入并乐此不疲往返于宿舍琴房间。现在英国的琴房设备良好,随意出入,我又岂能不好好珍惜?在资本主义社会有琴可弹,是顶着学费、生活费昂贵的重担下唯一让我略感欣慰之处。琴房分设在音乐中心的两层,尤以楼下的石室为佳。石室的温度较之别处要低,置身其中,一股寒气袭来,一摸石壁,顿觉彻骨冰凉。当年杨过睡在活死人墓中的寒玉冰床上练内功,一年抵得上平常修炼的十年,莫非英国人也深谙此道,特意设此石室以助有心人修习上乘琴法?不过认真地说,每每意乱烦躁闷头闯进这石室时,倒是很快便心火自清了。石室虽然都有双重门与外隔绝,但是还是可以依稀听到其他隔间的声响。音乐中心当真是高手如林,蜗居石室,墙那头时而传来一长串无比清脆漂亮的花腔女高音,时而传来一大段极其绚丽辉煌的钢琴华彩,而这时候,我那几首简单的入门曲顿时相形见绌,我也禁不住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甚至陶醉其中忘乎所以。也曾经有一次弹“Fur Elise”,隔壁的Saxophone居然跑来合奏,没想到Sax版的“Fur Elise”是如此的情深款款,我不禁慢下节拍,附和着对方的韵律。体会着Sax固有的细腻,一呼一吸均是那么的耐人寻味,我不由得对着墙那头想入非非…… 直觉告诉我,演奏者绝对是个风度翩翩楚楚不凡的美少年。Sigh! 若不是深受东方矜持婉约的毒害,我早已识其庐山真面目了。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心底留下的是一朵无瑕的美。
音乐中心的琴虽然不差,但却不是最好的,全校可利用资源中最好的琴在音乐中心旁边的教会。那是一架卧式钢琴,不仅外表美丽,音色也几乎无懈可击。当大厅所有的灯都打开,端坐此琴前,顿觉优雅,亦恍如置身一场个人演奏会。每次路过那儿,如果里面没有人,总会雀跃地跑进去狂弹一番,心中除了感谢上天的恩赐外,别无他想。然而,小人博士却悄无声息地从天而降――
那一天拉开许久不动的窗帘,天空蔚蓝一片,小树也吐出绿芽,不知从何而来的坚毅让我关了电脑,决定出去走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觉就像闭关修炼七七四十九天后重见天日般的痛快。尽情拥抱着自然,脚惯性地朝着艺术中心的方向迈去。路过教会,无人,窃喜。
钢琴放置在大厅东北方向的角落里,侧边以落地玻璃与外面的草坪相隔。望着外面青青草地,甚是惬意,手指自然而然便弹起了“快乐的农夫”。我从不是个好学生,比如以前老师要求每次弹琴前要先练习音阶,让手指做好热身运动,我却从不效仿,随心所欲,总是想到什么就弹什么。再比如别人学钢琴一般是从哈农、汤姆逊之类的练习曲学起,而我与五线谱刚认识,就跑去找了一些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谱,硬是埋头拙练。上了几次钢琴课,觉得老师的进程太慢,干脆自学。所以我的基础十分薄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技巧不易提高。
有些小品还是比较喜欢的,比如巴赫的“G大调小步舞曲”和舒伯特的“f小调瞬间曲”。这些作品似乎数弹不厌、日久弥新,每次总能发现新的问题,例如最后结束的音符,力度小了显得结束过于突兀,大了又犯了矫揉造作之嫌。连、断、急、缓……处理稍差一分,效果却有天壤之别。静静地体味着这些,我弹完了“G大调小步舞曲”,突然,响起几声清脆的掌声。循声望去,屏风后探出一个脑袋,还有一双手掌。“Very good”来者说道。
我微微一笑,继续练习。来到英国已有半年,早已习惯老外友好的夸奖。英国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喜欢跟人说好话的民族。他们对别人的评价至少是抬高了一个八度,“Very good”实际上也就等于中文的“一般”或“还行”。
再次意识到循序渐进的重要性,我开始在键盘上爬音阶。速度——速度!力度——力度!满脑子都是这些念头,我越爬越快,越敲越带劲。突然,有个黑影向我这边移进。抬头,这次我看清了。来者是位老人,一脸俊秀,身体看着也算健硕,却拄着双拐,虽然拄着拐杖,却来势汹汹。更加奇异的是他脸上的表情,严肃、冷峻。突然有股莫名的害怕,我战战兢兢地问道:“你要用钢琴吗?”
老者来到我身边,低头说道:“你在爬音阶时可有将她们分段?”虽然语调不冷不热,但是眼神却布满慈祥。
“嗯?嗯……我不清楚,好像没有这么想过。”
“看着……”老者左手拿过右边的拐杖,腾出右手,在键盘上甚有节奏地爬了一个音阶,然后学着我急促地又爬了一次,“感觉出其中的差别了吗?”
我傻傻地笑了。
“哪一个更好听?”
“呵呵,第一个更有味道。” 想来老人家这么激动地跑来,是因为听不惯我对音乐的亵渎,只好出面制止了。唉!
“你刚才弹巴赫弹得很不错,你的乐感也很好,但是爬音阶只求速度和力度会使整个练习过程黯然无趣,这不是音乐所应带来的。”老者于是打开琴盖,又比手划脚,跟我说了很多钢琴的发音原理。有很多物理词汇甚是生疏,不过主旨我还是听出来了,就是要以柔制刚,大有太极拳“四两拨千斤”之妙。
感觉老者是位高人,于是力请老者演奏一曲。他也甚是爽快,将双拐往地上一掷,解下护腕便坐定开始了。只见他双手在键盘上迅速移动,每分每秒十指几乎无一空闲,覆盖范围之广可谓波澜壮观,手指动作之快可谓幻影叠生。我看傻了,笼罩耳边的是此起彼伏、丰满剔透的美妙乐章……曲终,我竟忘了鼓掌,等回过神来,才记起“登峰造极”之说。
老者问:“你可想跟我学琴?”
惊喜……忘言……
后来才知道那天师父弹的是一首肖邦的狂想曲。师父早年毕业于牛津,一家大小皆喜好音乐。几个小孩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目前也都长大成才,不时会参加一些演出。
故事仍在继续着。师父抽空会来学校传授一点心得。除了第一次上课没带笔记本老人家有点不悦外,进展还算顺利。
写到这,突然觉得故事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尽管过程的确有点出乎意料,但是以后回想起来也必定归于平常。一切始于平淡,也将止于平淡。
附记:一篇旧作,写于2003年春英国华威大学。那时我正在英国读书,那是一段朝气洋溢的时光。
作者介绍:肖淳端,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海外华人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暨南大学杰出青年学者、“双百英才”,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理事,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世界族裔文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广州欧美同学会理事;曾任伦敦ECI译员,为BBC等电视台编译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