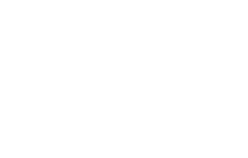【戏说英国】追忆托笔先生
作者:吴帆
说到英国,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青少年时代,狄更斯、毛姆、伍尔夫、奥威尔、勃朗特姐妹等作家的作品开启了我对英国的启蒙教育,此后我的书架上陆续出现了石黑一雄、奈保尔、麦克尤恩以及巴恩斯等作家的名字。那时,我虽然还没有去过英国,但感觉自己似乎了解不少英国的历史人文,还有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令人惭愧的是我其实总共只去过英国三次,而且每次时间都不长。我的真实世界里的英国经历是一个个分散的小片段,而不是人物场景连绵不断的卷轴画。它们都和我的第一位文学代理人托笔·伊迪先生相关。这些片段影响了我的人生,每次想到它们都让我充满温暖和感恩之情。
几个星期前,我的英国出版人邀请我明年夏天去英国参加我的新书《被遗忘的灵魂》的读者见面会。这本七年磨一剑的长篇历史小说写的是一战期间英法招募的14万赴欧中国华工的故事。和她通完电话后,我眼前浮现出托笔先生的身影。虽然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和他谈及这本书的写作,但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想起他。是他让我走进了西方的出版界,也是他鼓励我在写作时要听从内心的呼唤。
第一次去英国是近2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正在为我的第一本英文小说寻找文学代理。白天全职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上班,晚上熬夜写作的生活几年下来让我颇为疲倦。在很多欧美国家,作家要通过有 “出版界把关人” 之称的文学代理才有可能把作品递到出版社编辑的手中。作家圈里有这么个说法,那就是找到合适的文学代理比找到理想的婚姻伴侣都难。在美国尝试找代理人近一年后,我收到的都是拒绝的答复,拒绝理由多半是说这本书过于中国化,很难在西方找到读者。有几位代理人甚至建议我对书做某些修改以便让它适合西方市场。抱着做最后一次努力的打算,我给英国的一家小型却很有名气的文学代理社写了封邮件,介绍我的小说,并附上了前三个章节。几天后,我居然收到在业界享有盛誉的代理社创办人托笔先生的回复,问我为什么要到英国找代理。我实话实说了,并按他的要求把整本书稿的电子版寄给了他。当时希望的种子虽然在心里发芽了,我其实并不认为会有什么结果。作家们都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即使文学代理读了作家寄来的书,绝大部分的时候他们的决定是一个字:“否”。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大约五点多,我的电话铃响了。担心在国内的父母或是亲人出了什么事,我慌慌张张从床上跳起来接电话。一拿到电话,就用中文习惯性地说,“喂”。电话另一头沉默了几秒钟后传来一位男士的缓慢而庄重并带着浓重的英国口音的声音。他慢条斯理地说了点什么,但是那时我的大脑的语言转换功能还没有开启,所以我一下懵了,想着他也许是打错电话了。他接着又说了些话,依旧不紧不慢,好像是大卫·爱登堡在做关于自然界的富有说服力的演讲。这下我听明白了。原来他是托笔先生!他说他读了我的书稿,非常喜欢,邀请我尽快到伦敦和他见面,还说他有个原则,那就是必须见到作家后才决定代理事宜。当天我向公司老板请假,一个星期后抵达了伦敦,就住在托笔先生还有他的太太欣然女士的家里。
到英国那天天气如何,一路什么街景我现在全然不记得,但我记得很清楚托笔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他是我想象中的学识渊博带着贵族气的老牌英国人(我后来得知他果然来自和王室有渊源的英国贵族家庭)。他60出头,满头银发,身材高大,步伐坚挺,目光锐利但又透着宽容。他说话富有权威性,有时视线会投向远方,好像那里有其他人看不到的宝藏。他打起喷嚏来力道十足,笑起来脸上则带着孩子气。他的家里雅致又充满情趣,到处都是书和艺术品,厨房餐桌的花瓶里插着一束鲜润的黄水仙。我特意留心了一下书架上的书,发现其中有不少我熟悉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我进门没多久,他就和我聊起了我的书稿还有中西文学现状,并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他谈到自己70年代就去过中国,此后又多次访问。他谈到西方出版界对中国的误区以及西方读者的偏见。说到兴起处,他洋洋洒洒,声音充满激情,让我很惊叹也很诧异一个不会说中文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如此深沉的爱和深度的了解。几个小时后,我见到他的太太 — 知名的作家和资深媒体人欣然女士。我和欣然一阵畅聊,有相见恨晚之意,同时我也意识到她对托笔先生的巨大影响。他们是出版界难得的中西合璧的知音夫妇。
第二天一大早托笔先生就起身了,看到我因倒时差无法入眠而在客厅看书,他邀我一起去附近的海德公园走走。看来这是他的日常惯例。出门前,他请我吃了他刚买的新鲜出炉的羊角包。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他手背在身后,气宇轩昂,大步流星,仿入无人之境。两旁的行人如遇到礁石的水流一样绕他而过。如果前面有座挡路的山,我想托笔先生也会以他的气势硬生生直通通开辟出一条隧道。海德公园树影婆娑,草地如茵,飞鸟蹁跹,其中美景自然不消说。不过我的注意力都放在和托笔先生的谈话上。我还不习惯他的英国口音,再加上他如教授上课一般旁征博引,我一走神可能就接不上趟了。何况我这个小个子还要加快脚步才能跟得上他的速度。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九曲湖。看到悠闲戏水的天鹅们,他的脚步放慢了,脸上绽开了天真的笑容,说,“你看看,它们是不是非凡的物种!”
两天后我返回美国继续当我的上班族,然而我的生活因为和托笔先生的相遇而永远改变了。短短两个星期,他不光把我的书的英文版权卖给了出版业巨头麦克米伦,同时还签售了多个语种的版权。一年后,通过他的牵线搭桥,我的短篇小说《猴年》在英国老牌文学杂志《格兰特》发表,而另一部短篇小说差点入围《纽约客》(后发表在 Ploughsares 杂志上)。
第二次我去英国是参加我的新书《二月花》在英国的发布会。托笔先生还有已成为我的好友的欣然在他们家给我举办了庆祝会。此前的一段时间,我在悉尼、墨尔本、新加坡、香港还有北京参加了当地的一些读者见面会以及文学艺术节。庆祝会上我碰到好些英国的出版人、媒体人还有作家。觥筹交错之间我看着托笔先生还有欣然忙碌的身影,庆幸自己碰到了良师挚友。这次英国之行有一个多星期,在庆祝会以及书店里的读者见面会之余,我随着托笔先生还有欣然游玩了伦敦及郊外的一些景点。一路走一路谈,尽享眼福和耳福。
托笔先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代理了很多作家,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畅销书作家伯纳德·康威尔(Bernard Cornwell),但他却认为他这一生能做十本好书就足矣,还说作家要写出一部好作品至少得花七八年。但他同时又是个现实主义者,知道作家要在竞争激烈,变幻莫测的出版界站住脚,那么每两三年甚至一两年就要有新作品。作为西方出版界少有的代理华人作家的文学代理人,他对翻译瓶颈和中西文化错位有极其深刻的认知。当我问他是否建议我写某些题材的时候,他很坚定地说,“听从你的内心深处的呼唤。” 在阅读我的描述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美丽如昨》的初稿期间,他常和我通话,讨论书中的历史背景,情节还有人物。虽然他有时并不赞同我的观点,但他总是耐心地倾听我的解释。
此后多年,我不光是托笔先生代理的作家,也协助他和欣然从事中西出版交流的工作,并和他们一起多次去中国。在中国出版界,熟悉托笔先生的人常常亲切地称他为“大托”。有一次,我和托笔先生和欣然一起去天津大学看望冯骥才老师。那天秋风萧瑟,雨意阑珊,一路上落叶纷纷扬扬。走在校园里,托笔先生似乎想着什么心思,他凝视远望,少言寡语,步履匆匆,身上黑色大衣的衣摆随风飘动,竟有些古代侠客的风范。不知怎么,这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数年后,当我得知他在和病魔做斗争时,我一时无法相信这个噩耗。他是笑声朗朗,激情满怀的大托呀!他打起喷嚏来能震住一房间的人!他怎么会得癌症呢?
第三次去英国是在2018年。前一年的平安夜,托笔先生驾鹤西去。欣然在火车站接我,她看上去瘦弱憔悴,头上多出了不少银丝。大托自生病以来,她既是他的秘书,营养师也是他的护士。第二天我们去了大托的墓园。大托沉睡于树木之间的草地下。嵌在地里的黑色大理石的方形墓碑上雕刻着翻开的书页,左页上写着:玛丽·威斯利和海因茨·齐格勒之子 / 欣然之丈夫及知音。右页上写着:热爱文学之人 — 睿智,慷慨,忠诚。左页脚是一束黄水仙,右页脚是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可爱的小鸟。墓碑周围环绕着白色的天竺葵和雏菊还有如峰塔一般的松果。当欣然和旁边一位也前来扫墓的老人聊天的时候,我在墓园漫步。清风微拂,一群小鸟从树丛间扑棱棱飞起,划过蓝色的天空。欣然常提到她和大托的心灵感应。那群飞鸟之中是不是有大托的化身?
亲爱的大托,明年咱们英国见,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