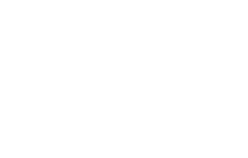Blog:【戏说英国】“红茶,不加奶,谢谢”:我和英式奶茶的二三事
作者:田天
英国人喝茶,往往颇费周章。虽然来这里生活也小有十年,每每看到,还总像是看西洋景儿般新奇。主顾进了舒服的小咖啡馆儿,要上一壶茶。不一会儿,服务生用纤细的双臂拖着个棕黑的大托盘,上面放着白瓷的茶具。茶杯碟上是肥硕的茶杯,茶杯里又套着个小巧的白瓷小奶罐儿,沿儿上微微突出个嘴儿。讲究的馆子还要在茶杯旁摆上小茶匙,甚至银质的小滤网,叠床架屋,看着就沉。有时候若是个姑娘打老远的柜台端来,不等走近,用耳朵就能察觉托盘在颤动,上头的茶壶盖儿不停地磕着茶壶边儿,茶缸子在白瓷盘子上微微的摇,清脆的响动絮絮叨叨,仿佛是茶壶里刚烧开了水。主顾恭敬地接过来,在桌儿上铺开这套茶具,倒茶、加奶、加糖,拿起不锈钢的小茶匙搅拌一番,又是叮叮当当一阵,过了半分钟,可算是呷上了第一口茶。远在东方,中国的茶客用紫砂壶浇着茶宠,一旁焚香弹琴;东洋的茶客静静地跪坐着,一把秀气质朴的茶筅翻动着瓷碗中的抹茶,都可谓是“茶道”。而英国人这叮当作响的喝茶程序,也算是西洋的一种茶道了。
然而初到英国的我,对英国人的茶道实为不屑。自恃来自东土,茶之故乡,何必在饮茶上学西洋。家父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迷上用紫砂壶喝茶。我临行前,亲自包上了个青瓷的小茶具。莲藕的造型,放下盖儿就是茶碗儿,剩下的莲藕托儿就是个迷你茶壶,不大不小,刚好够一个人喝上几小杯,在异国他乡,总能怀念起故国,岂不美哉?然而每日功课繁忙,茶也从雅兴之源堕落为提神药汤。焚香弹琴,烧水洗茶的仪式早就跟不上伦敦城里快节奏的生活。每天早上,掀开纸盒子,两个指头夹出个英国早餐红茶包,丢在大茶缸子里,一壶开水浇下来泡到发黑,几口喝下,颇为狼狈。然而即便是落魄到茶道尽失,我依然保留着最后的一点尊严:喝茶不加奶。这是多年来的习惯,也是心中认定喝茶最本真的方式。虽说我上大学那会儿见证了珍珠奶茶的勃兴,但是打那会儿我就颇为保守,满打满算,四年里也就喝过不到10杯罢了。驱车北上来到青城呼和浩特,当地的锅茶里,咸奶茶咕嘟着,里头的奶豆腐和炒米翻滚着,第一次去内蒙就被它俘获。然而尽管喜欢,也不是能天天都喝得上的,即便去喝也更像是体会草原的异域情调。真的要喝茶的时候,一壶水,一把红茶,简简单单。
然而没想到在喝茶上自视甚高的不仅是我,英国人也是如此。这就让我和英国人在喝茶上曾经水火不容。加奶不加奶,若加奶,是牛奶还是豆奶;加糖不加糖,若加糖,要加几个茶匙,甚至茶匙里的糖是冒尖儿的还是平的,糖是白糖、红糖还是木糖醇...这些个问题就和英国人丁零当啷的喝茶程序一样,一桩桩,一件件压到主顾身上,点上一道茶就跟买保险签合同书一样琐碎。也难怪英国人把一个人喝茶的这些个琐碎的喜好称为Tea Policy, “饮茶政策”亦或是“饮茶条款”,小小一杯茶如何喝就如同国家大事般严肃。对坐喝茶的两人不同意彼此的“茶策”就好比两国间断交开战般剑拔弩张。甚至有些人以自己的“茶策”为荣,成为自己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好比说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工人,就以红茶加奶和两匙白糖为标志,若是不这样喝上一杯,下午就打不起精神。而这种茶久而久之也得了个“工人茶”的名号。于是乎,即便是到一个炸鱼薯条的摊子,要的茶也是仅仅是五大三粗地装在白瓷大马克杯的,忙得蓬头垢面的老板娘也要在百忙之中,攥着小本儿和圆珠笔,小心翼翼地问我,我要加奶还是不加奶,加奶要多还是要少,还是差不多就成,生怕挑起一场战斗。而我的“茶策”也可能是英国上下最简单粗暴的:茶,别的不要。然而就是这么一条简单的政策,在当地人看来却颇为奇特。我和英国人普遍“加奶加糖”的“茶策”也就有了冲突。虽说没到“召回外交人员”的程度,但是也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事儿来。
到英国的第一年,我还是个初来乍到的研究生,窝在管早饭和晚饭的学生宿舍,名叫爱佛依梵(Ifor Evans)。每天早上七八点钟,下楼来到食堂,拿起盘子,从打饭的阿姨们那里接过烤香肠、煎培根、炸薯饼和烤豆子,边儿上撒些蘑菇,再码一个烤得略焦的西红柿,便是一顿英式早饭了。然而,自秋天到次年夏天,每天早上都是香肠培根,未免单调油腻,即便丰盛也吃不下去。于是乎茶就成了去腻消食的汤药。每天打完饭,未等坐下,先踱到附近的热饮机器前,从一旁拎出一个白瓷缸子,打上一缸子红茶。一股黑色药汤般的红茶直直落下,热气腾腾。我每天就着红茶咽下肥腻的早饭,却不知道我早已被一双好奇的眼睛给盯上了。食堂里头,总是有个清洁工立在角落,蓝色的短袖,露出黑粗强健的手臂,双手握着拖把,一双眼睛好似乌木雕像上镶嵌的缟玛瑙,硕大的眼珠咕噜噜地转着,看着来往的我们,好似个人类学家。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径自一人坐在个大桌子上,正吃喝得出神,便看到他慢悠悠地来到我桌子对面,拉出椅子,不紧不慢地坐下,眼睛则一直盯着我,仿佛是见到了野外的小鹿,生怕把我惊跑了。他坐踏实之后,强壮的双臂放到桌上,身体向前倾着,小心地低声说:“打扰了,我能问您个事儿不?”
“行啊。” 我点了点头,心想可能这位想学点儿中文的寒暄罢了。心中瞬间开始把“你好”、“再见”排了个序,把“谢谢”排在了最后。心想英语国家的人,多数发不出“谢”。
“我看了你快一年了,有一件事儿我不太明白。” 他的眼珠往下轱辘,落到我右手边儿的白瓷缸子,里面是冒着白气儿的黑汤儿,“您喝茶怎么不加奶啊?”
我当即一愣。心中一方面抱怨白准备了这些个寒暄,一方面又想不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最后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我打小在中国就这么喝的,习惯了。” 这位专业清洁工、业余人类学家点点头,道了谢便走了。
专业的人类学家都说,有时候,被采访的当地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做一些外人看来不太平常的事儿,于是乎就编一个解释搪塞。我那会儿何尝不是呢?喝茶不加奶真的仅仅是习惯使然?还是背后藏着点儿小心思呢?扪心自问,多年来,我确实把如何喝茶和如何为人挂钩了。坚持喝茶不加奶,与其说是坚持自己的“饮茶政策”,不如说是执着于一种人生态度。茶之为茶,在于苦涩。红茶入口,莫急着咽下,让茶水带着那苦味,给口中镀上薄薄的一层膜,洗去了所有餐饭的油腻。缓缓呼气,回甘自来,在之前苦涩映衬之下,弥足珍贵。国人的文化,讲求的就是吃苦忍耐,而后苦尽甘来,和喝茶的方式完全一致。
英国人则不然,似乎完全喝不得这苦涩,要让牛奶遮掩,方能入口。红茶注入了奶,虽然多了层香气,却也消弭了茶的苦涩。之后的回味也伴着牛奶温婉的香气而来,少了一番苦尽甘来的气息。有的时候,奶中的脂肪,和早餐中的肥油沆瀣一气。一阵肥美油腻的香味扫过之后,留下的是黏答答的狼藉。喝茶如此,过日子更是如此。英国人似乎特别善于给生活中的苦涩上,加上点奶。下午三四点钟,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捧着纸杯子,喝茶聊天,五六点钟却下班了,毫无昂扬奋进的样子。晚上七八点钟,街上五颜六色,琳琅满目的小店和酒吧喧嚣不止,毫无质朴耐劳的气质。这样回避苦涩,享受安逸的国民,怎能让国家强劲向上,得到国力发展后的回甘呢?自视甚高的我心想,自己万不可以接受英国人这种沉湎于安乐的态度。虽然嘴上不说出来,但是每次要茶都会倔强地告诉对方:“劳驾您,红茶,不加奶,不加糖,谢谢您。”
然而英国人却不领会我的“茶策”,隔三差五就往我的茶水中兑上牛奶。我心中颇有不悦,但是始终没有胆量抱怨。午饭的时候,往往在学校周遭的咖啡馆凑活一顿。一个三明治,一杯茶,十分钟里风云际会,不待细嚼慢咽,甚至最后一口还在喉咙里,就已经起身回办公室了。要茶的时候,我经常直接说“Black tea”。大多数情况下,对方就知晓了,这位主顾不加奶。然而咖啡馆里往往嘈杂得很:大声的流行音乐,往来人群的说笑,咖啡机的隆隆轰鸣,这就让我说出的词儿,到了对方耳中,能没了一半儿。原先的“Black Tea”,经过这番过滤,就剩了下了“le”和“tea”。对方也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耳朵里钻进了“le tea”之后,就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我做了一杯拿铁咖啡 Latte,还拉出了个颇为精致的奶花来。我接过这杯咖啡,只能一阵苦笑,心说也算赚了,拿铁咖啡好歹比红茶贵了那么几分钱。然而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明明是为了避开加了牛奶的红茶,说了Black Tea,最后换得的,反而是杯加了奶的咖啡,南辕北辙,不过如此了!这种事情多了,自然觉得仿佛整个英国和生活都在和我作对。喝一杯不加奶的红茶,有这么难吗?
说难,也不难。红茶不加奶,就是要其苦涩和回甘。而当时的生活,已全然不缺苦涩了。攻读博士的前两年,白天钻研史料,撰写报告;日落后,龟缩宿舍,蜷在桌前,翻译书籍。不到几个月,脖颈痛到不能点头,两肩僵硬摆臂不得。而驱动这副破烂躯体继续工作的,正是一杯杯漆黑不加奶红茶(亦或是不得不喝的拿铁咖啡)。苦涩之后,回甘自来。十一月的伦敦,黑色的树干顶着或红或黄的残叶,街市上点缀着深绿的冬青和金黄的落叶;灰色的天空,西边的乌云突然被划开了一角,露出屡屡落日的光辉。一时间温暖和冷清,生命与死亡交相辉映。四体疼痛的我撂下手里的工作,一瘸一拐地漫步在一丝灵顿(Islington)的大街小巷,以求内心的平静。沿着安为大街(Amwell)踽踽南下,突然望到左侧瘦削的圣马可教堂高塔,被夕阳染成了金黄,刺向灰色的天空。四周映衬着或绿或黄的树冠。四下无人,唯有鸟鸣。若是普通的时日,这番景致不过尔尔,但是在苦涩的工作后,这静谧的教堂,平静的秋景,却格外地喜人。以至于距今已有六年,提及那段时光,就会有个哥特高塔突然从脑中钻出,刺到我的眼前。
然而,过日子真的和喝茶一样,总有不知道打哪冒出来的一股牛奶,注入你的茶汤。冬去春来,我的生活中多了一个人,我未来的夫人。读书漫步之外,生活里多了一番陪伴和温情。她说周末里我应该放下工作,修养身体。于是工作之外,我的生活里有了公园里的私语,四体的疼痛也神奇地消失了。我们俩每天早上会一起在学校附近的小咖啡馆喝一杯茶,再开始一日的工作。如胶似漆的我们,共享着一杯红茶,但是和往常一样,这杯红茶红得发黑,两人一起在经历着苦涩后的茶香。告别恋人,来到系里,遇到导师,谈得也不仅仅是学问,而是如何注意颈椎健康。我的第二导师是个活泼大气的苏格兰人,一日匆忙间见我拿着一块司康饼,捧着一杯红茶,愣是停下脚步,退回来,对我说:“司康饼以后要加奶油和果酱才有滋味”。办公室里,到了三四点钟,同事们拿起纸茶杯,三三两两说着小话儿。有一天,我也摘下了耳机,回过头去,拿起了自己的茶缸子,丢进去个茶包,端在手里,加入了闲谈。有时候说笑间就有了灵感,真是“不知道那块云彩有雨”。
苦涩的日子最后还是消退了,而有一天,我当突然感受到了口中逐渐褪去的茶的苦味,心说不好,我的红茶里,开始一点一滴混入牛奶了。然而,恋人、师生和同事关系中的种种欢乐和甜蜜,远比苦涩后的回甘更有滋味了。或许,红茶里加点奶也未尝不可。何必死守着自己多年来的“茶策”而抛弃英国奶茶的清甜?于是乎,有一天,夫人问我:”这次咱俩的茶是不是加一点奶啊?” 不久之后,我端着一杯茶,黑色的茶水被牛奶染得花白,回到了她面前。从那次之后,我们的餐桌上,也响起了白瓷奶罐子、茶杯和小茶匙碰撞的叮叮铛铛,一杯杯红茶变为一杯杯奶茶,茶香和奶香交汇,不见了对苦涩和回甘的执着。不过有时候,当我只身一人,进了茶馆儿。要了茶,提楼起那小奶罐,我会突然忆起故土青山下鳞次栉比的水泥居民楼,忆起家父装饰着松枝的紫砂壶。那个刹那间,我突然放下了小小的白瓷罐儿,举起茶杯,抿了一口苦涩的红茶,熟悉的苦和涩爬满口腔,而就在茶香慢慢显现的时候,我又举起了奶罐。白色的牛奶氤氲在黑茶汤中,仿佛水墨交融。加奶,不加奶,最终由得我来决定。拥抱英国生活里的安逸,还是坚守故土对吃苦的追求,也最终在我的一念之间吧。
作者介绍:田天,伦敦大学学院埃及考古学博士,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系研究助理。在英求学工作近十年,好以文章介绍英国历史人文。